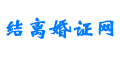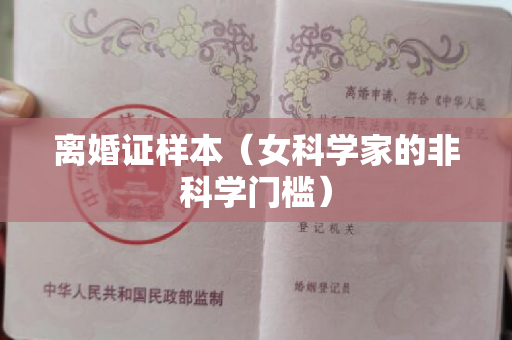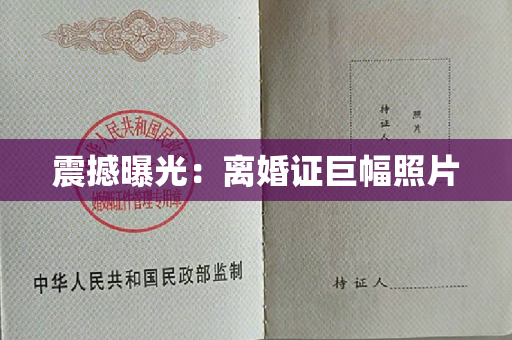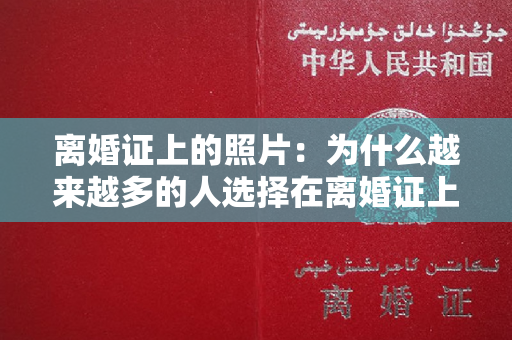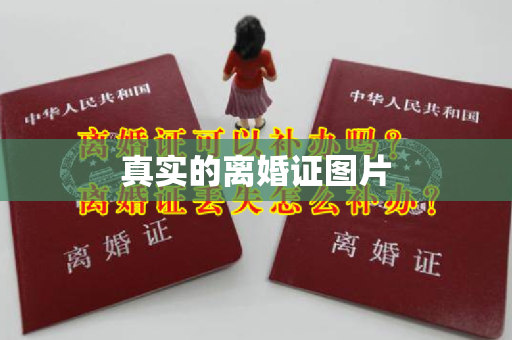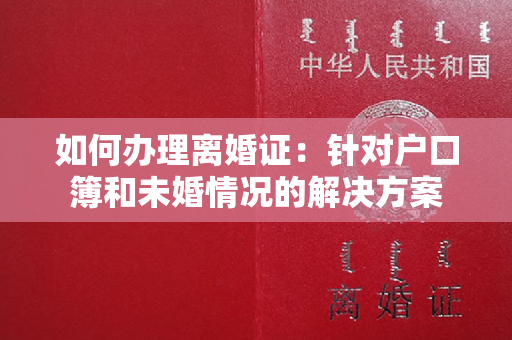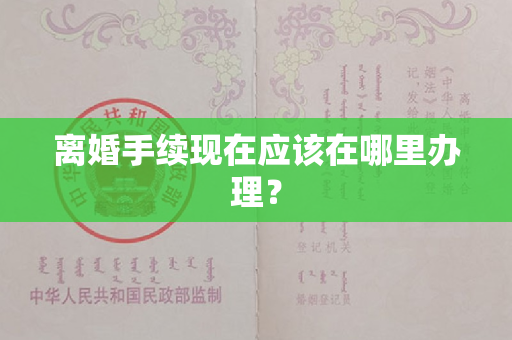离婚证样本(女科学家的非科学门槛)
10月14日上午,浙江绍兴,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3世界女科学家大会举行。大会介绍亚太地区女性参与科技创新的调查情况,发布2023世界女科学家大会绍兴倡议。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视觉中国提供
6月2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召开对女性科研人员资助政策调研会议。受访者供图
即将进入“非升即走”的第三年,秦晓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一年,她还没参评副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第二年落选,在承担科研工作的同时还在兼顾学院的行政工作。“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在秦晓的计划里,“明年拿下青基,评上‘副高’就备孕”。
但现实是她33岁了,已经不在“最佳生育年龄”的序列。
孕5周,秦晓第一次在“屏幕上”看到了孩子,这个10毫米的“小糖豆”一下就攥住了她的心,“我没有刻意备孕,但她长得这么好,所有指标都正常”。
秦晓决定生下这个孩子,同时开始准备三战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虽然截止年龄是35周岁,但对我来说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申请了。”秦晓担心自己生完孩子之后的两年没有体力和精力再战“青基”。
从拿到博士学位,到教学、科研、发表论文,一个女性学者在职业阶梯上“最难熬的10年”往往是她们的最佳生育年龄。研究员张琴曾经在一场科研工作会议上听到这样一个建议,希望女性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年龄线可以适当放宽,男性保持不变。
各类科研基金青年项目不仅为学者带来丰厚待遇和学术资源,在一些实行“非升即走”政策的高校里,获取某项国家级科研基金项目是青年教师获评职称的必要条件之一。一些青年学者不得不集中调度自己的时间,赶在年龄节点之前,匹配高校的学术评价。
其实,早在10多年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就将女性申请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年龄限制由35周岁拓宽至40周岁,旨在为女性创造更为友好的科研环境。
3年前,科技部、全国妇联等13家部门发布《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其中明确提到,国家人才计划适当放宽女性申报人年龄限制。
但是,在女性学者相对更为集中的社科领域,这项变革仍未全面推动。事实上,在我国,除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部分项目对女性有特别支持之外,其他类型的科研基金项目鲜少区分男性和女性申请者的年龄限制线。
在张琴参加的关于女性婚育研究的科研内部工作会议上,上述建议引发了与会学者的讨论——年龄不再成为限制条件,是否会真正激发女性的科研创造力?从另一个角度看,以性别区分评价标准是不是“另外一种不平等”?
直到自己开始备孕,张琴才真正理解了那场会议上的争论,以及女性学者面临的困境。
生还是不生?什么时候生?对于一些女性学者而言,生育的选择甚至关乎科研生命。张琴博士毕业时29岁,那时候的她并不觉得女性一定要生育,“丁克夫妻”是学术界常有的组合。
一次拜访给了她很大的触动。张琴的师爷90多岁了,家里没有孩子,只有一台扫地机器人,“他看着那个小东西,来来回回的就像看着一个小活物一样”。师爷住在大学的家属院里,楼下就是附属幼儿园,放学的时候,孩子们成群结队,叽叽喳喳。师爷有时站在窗口望,有时直接到楼下去,他告诉张琴,“年轻的时候觉得他们好吵,但是退休了之后,就特别喜欢听那些小孩的声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渴求特别有生命力的链接,张琴说,“我其实是怕自己会后悔,等到我真的想要的时候,又不能生了。”
博士毕业后,她进入一家体制内的研究院工作。她的办公室藏在一栋大学的行政楼里,每周她需要到单位坐班两天。相比于高校,这里的晋升压力和发表论文压力都没那么大。张琴结婚时31岁,在博士师门里不算晚,“但我第一波结婚的初中同学有的已经开始离婚了”。她告诉记者,晚婚的女博士在生育时机的选择上往往面临着更小的容错空间。
“生育的线好像也卡在35岁。”备孕中的张琴发现,20多岁的女性做孕检大多没什么问题, 但是到35岁以上,指标经常有“红箭头”。
35岁同样是一些“青椒”(代指青年教师)最重要的聘期截点,决定了她们是否能评上副高职称,通过“非升即走”的考核,一旦失败就意味着失业。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李秀清曾在其文章中提到,各高校竞争的第一硬核就是科研学术,重中之重就是科研、发文、重大项目。
高校里的女性“青椒”延后生育有时是一种“不得不”,“在年龄线之前,先拼项目”。一方面这些科研基金项目影响着科研人员的职称、待遇和资源分配;另一方面,有了自己的项目和经费才能更好地攻克科研问题,“以项目成果为包装的科研论文更受期刊的关注”。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世杰、张文霞在调研中发现,一个青年科研人员如果在职业生涯早期未能实现高起点,就很难在后续职业生涯中实现突围,所以青年科研人员从一开始就要参与激烈的资源角逐。
在社交平台上,科研人员把国家级科研基金项目的公布时间称作“放榜日”,青年项目被他们看作科研之路上“升级打怪”的第一个关卡。有人发帖“35岁拿不到青基怎么办”“拿不到青基是不是这辈子都评不上副教授了”“最后一次青基机会,如果不中科研道路怎么走”……
李秀清发现,相较于她刚入职的时候,30年后的现在,若要在高校立足生存,求得发展,需要应对的任务重了不止一两倍,青年学者面对的压力与日俱增。“毋庸讳言,这对年轻女性学者的压力更甚。”
她曾在学校的一场内部会议上建议,针对科研考核和评职称的量化机制,应给予职称升迁期怀孕生子的老师至少两篇核心期刊论文的加分,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认真的。”李秀清说,“男人不会怀孕,不会分娩,不会哺乳,女性对此的感受必然会更加强烈些。”
上海交通大学在2020年曾进行过一项研究,探讨“非升即走”制度下女性青年教师的压力状态与生育意愿。结果显示,因惧怕求职中对未育女性的性别歧视,16%的被调研者经历了生育提前,52%经历了生育推迟,大约33%评上副教授才生育头胎——在职业生涯最黄金的时期,女性要面临生育和升职的两难。
“生育最好的时机要么早要么晚。”在张琴的观察样本里,硕士研究生阶段就结婚生育的师妹似乎在教职工作中没有那么窘迫,但她仔细想了想又补充道:“她的父母非常给力,一直帮忙照看孩子。”
一位教授妈妈表示,常有邻居羡慕她,一周就上两天班,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在家带孩子。但其实,科研工作的弹性制意味着“永无尽头”地思考,就算没有时间和精力实现高强度写作,也要保持阅读。“甚至是我有了孩子之后才意识到,我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
“不发表,就出局”是学术现实,科研人员在科研与教学的夹缝中“谋生存”是常态,这与人们对高校教师职业自由轻松,有更多闲暇时间照顾家庭的认知反差明显。
这也因此强化了女性学者的困境——“在学术职场努力谋生存的同时,还要面对家庭成员对其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的期待。”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关于女性年龄限制的改革在10多年前就已先行,考虑到女性的生育周期,放宽女性的申请年龄。在张琴看来,如果这项改革扩大至其他科研基金项目,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其他学科女性学者喘息的时间和选择的空间,这或许并不能全然解决当下女性面临的科研困境,但仍然可以发出一种声音——“你可以选择,不必放弃。”
但这并非对女性的“特殊照料”,杰出的女性科学家们已经证明,女性可以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
10多年前的改革在当下有了可查的结果。
202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基金项目女性申请者占比51.15%,略超过男性。而在2010年,青年基金女性申请占比仅为36.5%。这样的变化正源于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颁布的一项措施——将青年基金女性申请人的年龄从35周岁放宽至40周岁。其实,在这项措施实施的第一年,女性申请者的数量占比就有了显著的提升——2011年,女性申请者的数量占比提升至47.5%。
毋庸置疑,改革措施的颁布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激发了女性申请的主动性。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一位工作人员表示,长期以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难度越大,女性申请者的数量越少。另外,男性在基金项目中的竞争优势更为显著,数据显示,从2015年至2018年,他们的获资助率始终比女性高3个百分点。
为了改善这样的现象,12年前将青年基金的女性申请年龄拓宽之后,后续的改革就已经在孕育中了。“科学基金一项重要使命是人才培养,从青年基金、优秀青年基金到杰出青年基金是自然科学基金委希望构建的人才培养链条。”优秀青年基金在设立之初便将女性申请年龄较男性放宽两岁到40周岁。此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还提出,允许女性因生育哺乳原因延长项目研究期限。
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明确将女性科研人员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年龄限制由45周岁放宽到48周岁,该项措施将于2024年起实施。
“当女性在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有生育计划,她的研究可能被迫中断一两年,我们希望把时间给她找回来,实际是让她与男性拥有同样竞争的机会。”自然科学基金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在一场调研会上,一位女科学家说到动情之处潸然泪下。她刚刚经历了工作调动,与爱人分居两地。眼下,她一边照顾孩子,一边适应新单位的环境,分身乏术。而类似的困境在女性科研工作者的身上并不罕见,女性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高度重视,设立战略调研的项目了解女性人才的成长规律,邀请科技管理方面的专家了解方方面面的情况,与妇联等相关部门联动调研。“出台这个政策需要有理论研究,也要有实践的经验。”
还有一群人的声音同样重要——男性科研工作者,“杰青的资助率现在只有8%,10个里面还挑不出1个来,那么男性是否会有异议——你给她们优惠我们怎么办?”
一位男性学者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这位老师说,“课题组里面的女博士生往往很能干,因为女生干各种事情都特别地细心专注,但是博士生毕业留校以后,慢慢地感觉女生投入的时间精力就不够了,与男生拉开了差距”。
大部分的男性学者都能理解女性的学术成长需要克服的困难和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在照顾家庭方面可能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也可能被禁锢于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面临“科研项目少”“可支配科研时间少”“受重视机会少”“能力提升机会少”等问题。“大家一致反映对女性科研人员在拓宽年龄限制上给予特殊处理合情合理,也势在必行。”
递交的科研项目申请书在学术界被称为“本子”,写“本子”是一项技术活,也是个体力活。在敲定选题之前,需要阅读大量的文献和重要的政府文件以及工作报告——在秦晓咨询的申报经验和攻略里,不少前辈都指出“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联系越紧密越容易通过”。从这些海量的资料里,找到与自己先前的研究成果相关的部分,才能确定最终的选题。
“每天下午3点,就像有一支巨大的针管,直接打进脊髓里抽走了我的精力。” “嗜睡”是发生在秦晓身上最显著的变化,她只好和学校商量尽量把课程都安排在上午,中午一边休息一边处理事务性工作。
下午2点-3点几乎是秦晓唯一一段可用的“科研时间”。因为只要过了3点,“文字就像小蝌蚪一样游进眼睛,游出脑子”。
其间,同样申请“青基”的同学和秦晓闲聊时提到自己已经开始搭框架了,她说,“那时候心里真着急”。当天下午秦晓意外地没走神,而联动反应是在接下来的几天她一直处于焦虑失眠的状态。丈夫看她脸色蜡黄劝她“多休息,别太拼”,秦晓的情绪彻底崩溃了,她冲丈夫怒吼控诉,“当时最听不得有人劝我休息”。
秦晓不敢偷懒,在她看来,学术是一个渐进累积的过程,几天不看文献,就会生疏,思考一旦“断裂”就很难接上。
直到孕中晚期,胎儿稳定,自己的早孕反应没有那么强烈之后,秦晓才能把自己的时间留给“写本子”。精读文献、搭框架、填内容,坐在电脑前写作对于孕妇而言并不友好,除了腰部酸痛之外,胸闷气短也是久坐带给她的症状,写久了秦晓就会不自觉地深呼吸,有的时候一口气“吸不到底”。秦晓用1个月时间完成初稿,“赶在系统关闭的前一天才打磨好提交”。
提交时,秦晓距离预产期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有一种宝宝陪我背水一战的感觉”。
出了月子,她忙活起修校论文,开始准备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的申请书。“以前觉得熬过怀孕,平衡科研和带娃不是难事儿。”
但现实并不如所愿。月子里,孩子因为着凉粪便发稀发绿,“根本坐不住,看不进去书,在平台上到处查”。几个小时喂一次奶,秦晓的时间被切成了一个又一个小块。每次思路被打断,秦晓都得“重连”,所以大多数时候,她都只能做一些细碎的修改工作,再没有整段的写作时间。
她和已婚已育的师哥师姐咨询经验,得到的方法是“晚上8点和孩子一起睡觉,但是凌晨4点就起床读书写论文”,可是“婴儿不睡整觉”。
秦晓发现,即使丈夫体贴,婆婆和母亲都来帮忙,她也很难给自己拼凑出一整段的时间,“好像是一种本能反应,孩子在哭我就总要去看看”。
当思考被一次又一次打断,科研进度无限期延长,一篇论文要花两天才能读完之后,她逐渐说服自己,就做“60分”的妈妈,她学会放权给母亲和婆婆。但她又总觉得亏欠,“如果没有这个孩子,两位妈妈的晚上8点应该在公园跳舞”。
与女性在科研基金申请上的状况类似,女性学者同样存在高位缺席的现象——2019年,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性别数据统计中,女性占比分别为6%和5.3%。同年,我国在读博士研究生42.4万人,其中女博士有17.5万人,占比达41%。
近10年来,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占比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博士学位。“世界需要科学,科学需要女性”似乎已经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但是,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在中级、副高、正高职称中,男性数量远高于女性,女性晋级难度随着职称提高而加大。
这些现象似乎反映了同一个问题——女性在学术职业阶梯上的流失不断增加。有人把这种学术领域的性别差异称作“泄露的管道”。
女性是如何从这个管道中被泄露出去的呢?
李阳是一位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同样也是一位二胎妈妈。因怀孕和哺乳不能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时候,她会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参加所有的会议。孩子3个月时,有一场重要的产业研讨会召开,她背着吸奶器出差参加。随行的男教授问她:“你怎么总去卫生间?”李阳白了对方一眼,没做回答。“有的时候穿着宽松的衣服,找个角落就得吸了。”
“没有企业会因为你是一个在哺乳的母亲而为你开绿灯。”在那场产业研讨会上,她前后奔波,为每一个表现出兴趣的企业详细地讲解,也会有些尴尬瞬间,比如没拉好的书包里突然滚落出奶瓶,胸衣被溢出的奶汁浸湿,外套上不小心留下的奶渍……但是比起一刻的狼狈尴尬,李阳在事后回想起最担心的却是“他们会不会介意我刚生孩子,猜测我精力不足”。
开完会,她必须马不停蹄乘最晚的飞机赶回家里,接班同样是“青椒”的丈夫。
当类似的困窘出现在科研基金项目的推进中时,“可能你手里刚申请到一个项目,可是你突然怀孕了,这时你的精力、体力、精神状态都处于生理性的困境当中”。张琴告诉记者,一般来讲社科项目基础理论研究要求的结项时间为3年-5年,应用对策研究一般为2年-3年,怀孕哺乳并不会让母亲的科研工作全部停滞,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女性都无法完成周期性的田野调查工作,几乎只能集中在案头和文献研究上。
一些严格按照时间表规划生活的学术母亲,为了获取整块的思考时间,会把科研时间放置在凌晨2点-4点,以期一段不被打扰的工作时间。
但是,与秦晓有相同境遇的妈妈不在少数,仅仅只是怀孕嗜睡或产后失眠这些不受控的睡眠问题都可以轻易地摧毁学术妈妈严丝合缝的时间表,扰乱他们一个周期的研究计划。
如果用一把标尺丈量女性的科研生命,高点可能出现在职业生涯的后半段。
南京大学教授余秀兰等人在研究时把女性的科研生涯划分为5个阶段,29岁之前,大部分女性尚未生育,刚刚开始学术生涯的她们用饱满的精力应对工作,发展迅速。但是在29岁到35岁这个阶段,大部分女性开始结婚、生育,发文数量下降,学术生涯进入停滞阶段。
35岁至47岁是女性学者学术生涯中的调整与重建阶段,此阶段中,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女性学者将生活的重心重新转移到学术研究上,她们的学术生涯在40岁时达到顶峰,这也意味着女性科研人员学术高峰期的后移。
但遗憾的是,学术的优势往往是一个渐进累积的过程。比如,在国家社科基金的申请上,很多女性因生养幼儿错过35周岁,就失去了竞争部分青年项目的机会。所以,40岁时,女性虽然已经进入高峰阶段,但与男性学者的差距仍然在拉大。
一些优秀的女性学者突出重围,越过种种困难,成为塔尖的5%,为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作出卓越的贡献,她们证明了女性可以在学术工作中取得非凡的成就。但这并不能得出一个结论:女性学者没有面临障碍。
权益保障需要系统性支持
张琴仍旧记得在那场科研会议上,反对者女性居多,“如果说是在同一规则下,女性取得成绩当然值得肯定,但是如果因为你是女性,条件就有所放松,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歧视或者是不公平?”这样一种观点出现在讨论中,“承担家庭责任本身就不是女性一个人的事,但是如果说男性也要承担家庭责任,其实也意味着他做科研的时间要削减,所以年龄的限制不能是针对女性一边要放宽”。
比如被称作含金量仅次于国家社科青年基金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就将男性、女性的申请年龄共同放宽至40周岁,一些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将申请者的年龄放宽至39周岁。
李阳和丈夫都是高校的“青椒”,他们的暑假被婴儿裹挟,轮流吃饭、轮流带娃、轮流洗澡、轮流睡觉。在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每人每天最多两小时办公时间。对于李阳夫妻来说最直接的困境是育儿支持。
寻找“靠谱”的托育机构无果,暑假刚刚结束,李阳就迫不及待地向婆婆求助照看二宝。目前他们只能在双方父母的支持下完成对下一代的抚育。
同时,她的大儿子在高校的附属幼儿园上学,李阳常常感叹,自己下午的第一节课还没下,孩子就放学了。李阳只好把他接回办公室,“他几乎认识我所有的学生”。这位教授妈妈的办公室里摆着很多乐高盒子,有时在桌椅下面还能搜出散落的拼图碎片,这全都是用来吸引孩子注意力的,以换取李阳在隔壁实验室指导学生的时间。
有时,李阳要回家才有时间处理“案头”工作。她先哄睡小儿子,再安排丈夫和大儿子玩,以此偷得一丝加班时间。有一天,小儿子睡了半个小时就醒了,李阳惦记着第二天的会议发言,怎么哄都哄不好,“忍无可忍地对着一个婴儿大吼,大儿子听到动静也进来了,他可能没见过妈妈那么‘凶神恶煞’的样子,忍不住流眼泪。”李阳说到这儿,眼眶微微泛红,“当时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只是小孩子,有一个甚至是婴儿”。那天,她冲大儿子大喊:“出去!”
这次不自控的火气让李阳后悔至今,“其实在发火的下一秒我就后悔了”。那天晚上,两个孩子已经熟睡,她细数自己因为科研压力对孩子发泄的愤怒和展现的不耐烦,自责不已。“其实和孩子相处的过程是我灵感的源泉”,科研问题要从生活和实践中发现,李阳在给孩子体检时,带孩子逛公园时,选购药品时,都曾发现过其中可研究和可突破的科学问题,而这也确实成为李阳当下在申报的课题之一。
如何做一个“游刃有余”的“带娃女学者”,李阳或许可以从美国教授瑞秋·康奈利和克里斯汀·戈德西的著作《妈妈教授》中找到灵感。书里介绍了选择什么时机生孩子,选择什么样的伴侣,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怎样利用假期,甚至告诉女性学者要“降低对房间整洁度的要求”“大脑疲劳时,选择处理邮件等工作”……这本书更像是“生活小妙招”的集锦——教读者将教授与母亲的身份和谐地衔接。
但是,仅仅告诉女性自身如何努力和顽强似乎并不足够,这本出版于2011年的著作中已经介绍了一些大学的“家庭友好政策”,比如,提供家庭保姆佣金、托儿所费用、子女大学学费等方面的补贴……
此外,作者提到,在美国约有半数的大学提供工作场所的托儿服务。
这似乎是对我们更有启发的内容,即如何为女性的职业发展消除制度性障碍。据了解,上海正在通过建设爱心妈咪小屋、加大普惠性托育供给等举措,解决女性科研人员的后顾之忧。
过去的几年,多部门联合下发了《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支持女性科研人才,主要包括支持女性科技人才获取科技资源、提高科技决策参与度,完善女性科技人才评价激励机制,支持孕哺期女性科技人才科研工作等。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多年来进行性别研究,她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将政策压力转嫁给高校或者科研机构,“比如说给女性延长考核期,对高校或者科研机构来说肯定是效率变低。如果政策只关注妇女权益保障,可能会导致雇主感知到雇佣女职工成本增加,反而增加了招聘时对女性的歧视”。
妈妈教授升级打怪时,她们的权益保障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的系统性支持。我们是否能建立更为友好的环境和措施支持女性科研人才,让她们能更加从容不迫地面对生活。这与科研基金的年龄限制有关,却又不仅与其有关。
(文中张琴、秦晓、李阳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雪儿 记者 从玉华 来源:中国青年报